流动性经济学|美元:嚣张的霸权与沉重的负担
邵宇、陈达飞
2021年5月至今,美元指数从90低位持续升至109,涨幅约20%,突破了前期高点,也证伪了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的主流观点:美元开启了长期贬值之路。
疫情期间,美国的财政赤字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美联储持有的国债份额创新高,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这似乎并未侵蚀美元信用,反而强化了美元,增加了美元资产的需求。这不符合教科书的标准叙事,却恰恰是“嚣张的霸权”的题中之义。虽然大多数经济体都有主权或超主权货币,但全球是一个大的“美元区”,美联储政策有显著的外溢效应,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国债利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美联储年内4次加息,其他国家被迫闻鸡起舞,全球各央行百余次加息,否则两者之间利差缩小,会导致这些国家资本流出,汇率贬值,甚至金融动荡,利差(如国债利差)其实就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支付的“安全溢价”。否则不足以抵抗美元的拉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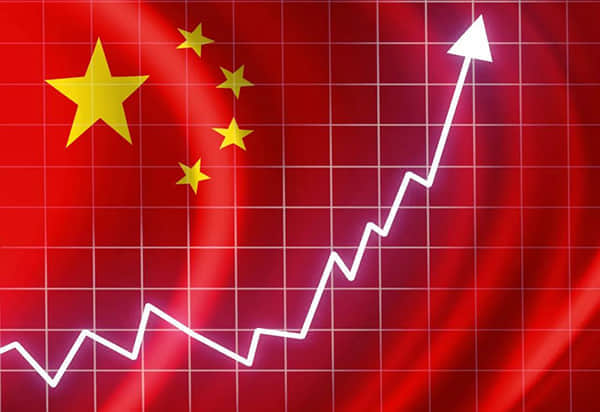
经验上,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汇率存在15-20年的周期变化规律。全球资本都受到美元的套利结构影响,每一波都可以说是美元的收割机时刻。一个美元周期的放松和收紧会伴随新兴市场许多波动,不少国家兑美元汇率也会有变化,美元一进一出之间,很多新兴经济体就会遭遇泡沫繁荣和经济萧条,典型的例如1980和1997两轮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疫情之前的高点出现在2017年初(103),按照7-10年的下行周期计算,美元下行周期应该持续到2024-2027年。
但是,新冠疫情(暂时地)中断了这一规律。因为,主导美元指数短期波动的是全球避险需求。每当出现“黑天鹅”事件,投资者都会追逐安全资产。虽然主导美元长周期变化的因素是美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在过去50年的3个周期中,美元周期的高点越来越低,部分就反映了其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所以早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关于美元霸权衰退的声音。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是不可置疑的,无论是在支付清算、外汇储备还是在贸易融资等方面,美元的份额都远超排名第二的欧元。
安全资产能为理解全球货币体系变革,进而为全球化的命运提供新的视角,这是因为,安全资产供给者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这两者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
对立性的表现是,美国在满足全球日益膨胀的美元需求的同时,也在创造对自身提供的非美元安全资产的需求,也就是说,创造美元的同时也创造了安全资产的短缺。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无风险收益率的下行是美元相对于其他非美元安全资产过剩的结果。
统一性表现在,美元和美债同属安全资产,同以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和国家信用为基础,只有在美债和美元被同时创造出来时,缺口才不会扩大,但这又在透支美国的国家信用和财政空间。
问题在于,是否会存在某个临界值,美债和美元是否会变成不安全的资产,从而遭到抛售?所以,美国财政部对外事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债主们不要抛售美债,或者购买更多的美债,尤其是在美国国内出现某种困局的时候。典型的案例是保尔森在任时,美国国内正在挽救金融市场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海外抛售美债,那就是雪上加霜。所以他曾经与中国沟通过这个问题,希望中国不要抛售美债。在这个方面,中美利益是绑定的,中国持有的机构债和MBS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国债,如果美国政府救市不成功,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嚣张的霸权”的另一面是沉重的负担。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贸易层面。美元作为“第N种货币”,决定了美国无法通过汇率机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其他货币大多钉住美元,可调整汇率以保持与美元的平价关系。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层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形成的美元体系,并未根除原有体系的内在缺陷——“特里芬困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美元与黄金脱钩解开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枷锁”,却打开了廉价货币的魔盒。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滞胀”,其次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国内信用的膨胀加剧了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与廉价美元相对应的就是安全资产的短缺,这被认为是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逻辑——“新特里芬困境”。
当权利与义务、收益与成本不对等时,全球秩序便进入非稳态。更确切地说,当美国感觉其从该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小于其付出的成本,或者,当其感觉搭便车者(free-rider)获得了非对称性收益,尤其是搭便车者还挑战了其规则制定权时,美国便不再有激励去维护该体系,甚至会主动破坏其建立的秩序。当前及未来,全球的两大主题是全球化的失衡与重构。
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说,2008年之后的世界与“大萧条”时期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方面是长期停滞。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借用其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并且,人口因素都是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旧秩序的终结和逆全球化的开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转折点是1913年,大萧条期间陷入低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建立新秩序,这一次的转折点是2008年,目前仍处在重构之中;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权解体危机。或者说,经济停滞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如战争和贸易战等,都是霸权解体危机的表现。
美元和美元资产的背后都是由美国的国家信用背书的,既包含硬实力,也包含软实力,从而也必然因为综合实力的相对衰落而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虽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元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在趋势和周期上,美元汇率与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高度正相关。
单极的美元体系,也将随着世界体系的多极化而趋于多元化。近年来,国际储备多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俄乌冲突之后该趋势或进一步加速。在绿色能源转型过程中,传统能源出口国的货币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或趋于强势,比如卢布、澳元等。不仅如此,贸易、结算、计价货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去美元化”的特征。这预示美元霸权开始出现其后期的一些特征和走向,其最终指向是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的多元化未来。
中国突围的关键是:第一,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国家能力;第二,在世界安全资产短缺的情况下,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弥补这个缺口。实际上,扩大金融开放,就是在弥补这个缺口。当前的短板是国家金融能力,也就是向世界提供安全资产的能力,其紧迫性不亚于科技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与人民币安全资产的供给是相互依赖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层次,这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外溢。实践证明,仅靠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阻力较大,空间有限。所以,未来或应加强人民币在后两者的体现,这分别要求中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建设健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前者主要依托于基础性科技创新能力和品牌能力,后者则依托于法律、监管等制度建设,逐渐消除金融抑制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两个方面,并非是独立的,因为研究表明,相较于银行信贷融资而言,权益类融资更有助于促进创新。
全球化总是在重复着失衡与重构、脱钩与突围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断变化,然而,从历史经验看,不变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虽然全球商品贸易面临逆流,服务贸易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而这恰恰是中国比较劣势的部门。类似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扩大服务业开放也有助于“补短板”,发挥后发优势。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还能强化本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金融、法律等服务业还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顺利走出去的关键。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编辑:吴家驹】
